2025.7.14 🌐 MariSwa.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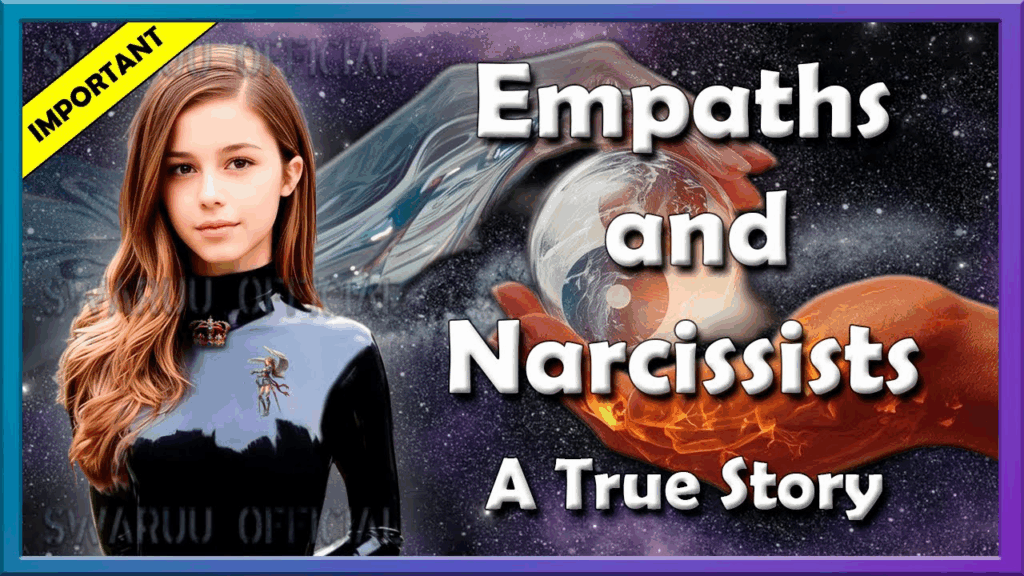
你好,谢谢你再次与我相聚于此,希望你今天一切安好!我是玛丽,最初的那个,唯一的那个,也是真正的那个玛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些信息可以被视为科幻小说,也可以按照观看者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看待,我发布这些内容仅为娱乐用途,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信息的,对于那些有洞察力的人来说。
这些从未被分享过的信息必须被说出,否则你们将永远无法得知。我是在2025年7月13日的早晨用英文写下这篇文章。
所幸,如今【自恋主义】是一个被广泛研究并且大多数人都熟知的主题,部分原因是互联网上有大量资讯内容,甚至油管影片也有介绍,因此,我预设读者已具备对此主题的先备知识与研究兴趣,所以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解释什么是自恋主义。
在任何一段关系中,最糟糕的组合之一,就是当一个自恋者成功掌控一位共情者。因为共情者,从定义上来说,总是会考虑他人的需求与愿望,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完整性与基本需求。
另一方面,自恋者只想不断索取与接收,回报则极少,仅仅是为了能继续剥削共情者,共情者只要觉得自己有帮助就会感到满足。
而自恋者正是利用这点,给予共情者一点点渴望的“残渣”,来操纵并持续剥削对方,却丝毫没有任何同理心,而共情者对此往往是盲目的。
这正是所谓“为他人服务”这一概念在地球和地球人处境中出现问题的根源——虽然它在许多进阶的星际与整体性文明中非常普遍。
无偿、无限制、无节制地服务他人,会让拥有这种心态的人沦为地球上无数冷血、无同理心的自恋者的受害者。
在地球上,若没有健康界限的“为他人服务”,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奴役,怀着无节制服务他人心态的共情者会成为自恋者的轻易目标。
自恋者根本不会尊重共情者那几乎不存在的界限,并会愈加变本加厉地要求更多。自恋者会利用任何能够侦测到、可作为“小恩小惠”的东西来操纵共情者,共情者则会把这些错误地当成真爱与友情,并继续给出越来越多、对方所要的一切,直到共情者达到极限,而到了这一刻,自恋者会羞辱共情者,说他一无是处、没用、充满缺陷,只为了再从共情者身上榨出最后一滴精华。
如果共情者再也榨不出什么了,那么自恋者就会摧毁共情者,然后将其抛弃。这一切都有充分的文献记录。
你们不必相信我,那些来自较为友善文明、成长于彼此和谐与互助合作环境中的星际种子与外星人,依定义来说本身就是共情者,他们都在努力适应地球这个敌意重重的文明,而这个文明与他们灵魂的振动频率截然不同,让他们难以理解。
在地球上所有善良的人当中,最容易在与自恋者的接触中受苦的就是这些星际种子与完全的外星人,因为他们往往连对方是自恋者都无法察觉。
现在,我将以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鲜明例子来说明这一切,我会以女性来代指共情者,但这绝不是说共情者只有女性,我只是想要澄清,在这个例子中,共情者大多是女性,虽然这个例子描述的是一个特定的事件,但这种不健康的互动模式在共情者与自恋者的关系中非常普遍,特别是在职场环境中,但不仅限于此:
从前,有一小群共情者,他们成长于一个更友善的地方,后来决定前往一个遥远且充满冲突的地区,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理念与信息,想要分享关于如何以更好、更不同的方式做事情的种子思想,他们完全是出于利他与理想主义的心态。
当他们抵达那个遥远而充满冲突的地方时,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谈,少数与他们对话的人最终也一再地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无法看见自己偏见与矩阵程序化以外的事物,这是因为任何矩阵尤其是地球的矩阵,总会试图透过不断的同化攻击任何异类,将一切压平、归一,凡是不寻常(异于常态之物)都会立即被贴上“虚假”与“骗局”的标签。
因为活在那个矩阵中的人们,只能依据他们自身的意识与知识水平去判断他们所见之事物,因此他们会诉诸于一些“半真理”的机制,比如奥卡姆剃刀: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我必须说,它只是“往往”,但不是“总是”正确。
这群刚到达那个遥远且困难之地的共情者,只一再经历质疑与嘲笑,直到命运的偶然与共情者与自恋者之间的致命吸引开始发挥作用。
这群外来的小共情者团体引起了两位自恋者的注意,这两人看中了他们视之为自我成名的机会,也能用来强化自己内在的不安全感与对认同的渴望,他们主动接近共情者,提出要代表他们(在社会面前替他们背书),而这些历经无数拒绝的共情者忽然看见了一个被肯定、被倾听的机会,得以兴奋地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资讯。
于是共情者犯下了一个错误:接受了由这些自恋者来代表自己,而不是选择继续独立发展、耐心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声望。他们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经历太多虐待后,内心渴望立刻被认可。自恋者开始代表共情者,但他们总是强调,是自己“施恩”般地替共情者分享信息给公众。
借此,他们得以全面控制叙事权,掌握哪些内容可以被公开,哪些不行。更糟的是,他们开始根据自身利益扭曲这些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能力不足以理解与记住全部信息。
他们并不在意信息本身的真正意义,而只关心是否对他们“有用”。共情者则继续以完全无私的方式自由分享信息,对他们来说,所需的一切只是来自自恋者那看似是“友情”的肯定,而在当时,我并不否认那也许确实是一种友情——从自恋者狭隘的现实认知中来看,以及从共情者那种盲目的“为他人服务”心态来看。
虽然这种心态在地球上根本行不通,随着这种不健康的关系继续发展,他们悄然、缓慢地滑入了奴役状态,出于对名声与肯定的无尽渴望,自恋者开始吸引越来越多想要利用共情者来达成自身目的的人,此时的共情者,不仅成为奴隶,还沦为一块被丢进充满凶猛食人鱼池中的“新鲜肉块”。
如我前面所说,矩阵会自我防卫,于是很快地,其他也以自身利益与贪婪为中心的自恋者开始攻击并诋毁那些已经在代表外来共情者的自恋者们,以及这些共情者本身,当然,在那些最初的自恋者心中,所有的诋毁与攻击,全都是因为共情者的无能与其所提供信息的错误所造成的。
自恋者从未承担任何责任,从未承认自身的缺陷与错误,没有人意识到大众所看到关于那些分享信息的共情者的一切,其实都是透过自恋者的视角与误解的滤镜所传递的,这导致了一种极端的状况——以至于大众甚至认为那些共情者根本不存在,认为他们只是自恋者为了牟利而虚构出来的幻想人物。
由此可见,情况有多糟糕,共情者不断地付出与付出,却什么也得不到,唯一收到的只有自恋者偶尔给予的一点点肯定与认可,而自恋者则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与金钱,而共情者作为彻底的奴隶,甚至连“存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但共情者仍盲目地不断付出、不断提供信息,只为换取那几丝友谊的残渣,与自恋者所给予的虚幻、操控性的爱。在成长的渴望下,自恋者改变了一切,并让一切看起来好像这份“扩展需求”其实是来自于共情者,由于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也想要剥削共情者的自恋者建立了联系,共情者因此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要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若是无法满足,他们就会再次被羞辱,被迫继续付出,不论是暗示还是明示,始终都受到“若不合作就会被所有自恋者诋毁”的威胁。
最终,共情者也走到了临界点,开始减少每日的信息提供,毕竟每个人一天内能做的、能写的都有极限;因此,其他与之合作的自恋者开始感到不耐烦,因为自己的期待与需求没有被满足,而当这个临界点被触及时,共情者已经无法再同时满足所有自恋者的要求了,这些自恋者开始大发脾气,导致了大量的争议与公众的不满。
当然,所有的责任又一次被推到了共情者身上,因为自恋者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他们的观点里,他们只是“好心”地帮共情者分享信息罢了,而大众仍只能透过错误的滤镜与视角来看共情者——这些滤镜与视角正是自恋者所设定的,他们总是根据自身利益去扭曲事实,同时将一切错误归咎于共情者的无能。
即便到了这种地步,自恋者仍声称自己是在“保护”共情者,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以及自身的利益,矩阵再次进行自我防卫,其他自恋成分浓厚的作者开始攻击共情者,因为他们认为共情者所传递的信息威胁到了自己的书籍与工作,而这些工作正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益。
于是,一如既往,责任又一次被推到了共情者身上——那些盲目听从其自恋操控者坏建议的共情者们,而他们所有想解决冲突的努力,无一例外地被自恋者的报复欲与对争议的渴望所挫败。
这情况发展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自恋者竟公然承认自己喜欢冲突与争议,因为他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他们将冲突视为一种宣传手段,认为这是生活中理所当然、自然不过的事。
身为标准的自恋者,他们完全无视共情者的需求与敏感,也漠视那些无谓争议所造成的伤害,而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自恋者依然持续榨取共情者身上的最后一滴资讯——这些共情者宛如奴隶,即使处于如此艰困的环境,也不得不继续提供内容。
因为自恋者不断要求更多、更精彩、更震撼的信息,好让他们能在面对接二连三的攻击时,继续被外界肯定,可是,他们依旧对共情者的需求视而不见。
共情者则仍抱持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就能说服攻击者与反对者,让他们承认自己的价值,但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
若对方心中早已做出否定决定,是无法被任何信息所改变的,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年、又数年,直到某些共情者终于抵达极限——她们的健康开始严重恶化,这一切都源于长期持续的压力,以及自恋者不断施加的高压虐待与她们所被迫进入的情境。
随着共情者无法再继续提供信息,自恋者对她们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双方间出现无数问题与争执,共情者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奴隶,然而,叙事权完全掌握在自恋者手中,因此这些争执从未被公众所知,公众所见到的是自恋者精心打造出的完美幻象:
一群看似完美、无瑕的朋友,仿佛只是无私地在为共情者服务,而事实上,共情者根本无法也不敢直接与公众对话,只因害怕再一次遭到自恋者的攻击,自恋者塑造出一个“完人”的形象,看似只为共情者的事业服务,公众轻易就掉入这个陷阱,根本无法看穿这其中极度不公平、残酷与剥削的实际互动模式——一切都发生在共情者与自恋者之间的暗处,那位主要提供信息的共情者最终崩溃了。
这时另一位介入:“别担心”,另一位共情者说,“我会继续提供资讯,否则他们会抹煞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努力就会白费“。
自恋者们继续以与对待第一位共情者相同的方式剥削第二位,一遍又一遍地,这种不健康且极度有毒的互动模式持续上演,伴随着不断由自恋者引发的争吵与问题,包括那些自恋者与共情者之间的严重冲突——这些问题从未对外公开。
因为叙事权仍然掌握在自恋者手中,然后,第二位共情者也因与第一位相同的原因崩溃了。
于是第三批人出现了,一如往常,当事情出错,是共情者的错;当事情顺利,则是因为自恋者那虚假而无懈可击的形象左右了公众认知。
这些第三批共情者持续像奴隶一样提供信息,只靠自恋者给予的虚幻友谊与认可维生,直到情势改变,而这时一位新的、不同的共情者出现了,这位最新的共情者曾经亲自来到这片遥远而困难的土地,因此对那里的社会互动早已有所了解,也能看清自恋者的本来面目,她同样有很多信息要分享,但她拒绝重蹈其他共情朋友的覆辙
她说:”不,我不要那一套,我要自己来“,她所需要的只是作为共情团体一员的身份认可,好让她能开始行动,其他共情者向自恋者请求这个认可作为一个人情,自恋者们不情不愿地答应了,因为他们视这位新来者为威胁,从一开始就对她态度恶劣。
后来,自恋者甚至声称这位新人的一切成功都要归功于他们,完全无视所有其他共情者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
然后,生活继续,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所有共情者都病得很重,重到无法再继续提供信息来喂养自恋者的地步,局势再次来到一个临界点,所有共情者都失去了行动能力,而这仅仅让自恋者们产生了无数的攻击与气急败坏的愤怒,因为没有新的信息到来,他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受到关注,他们完全无视共情者的处境,依然无情且残酷地持续逼迫共情者提供更多信息。
这场崩溃是决定性的且是不可逆转的,由于再也没有其他共情者能提供信息,那位本来就已经在独立传递信息的新人共情者开始全面接手所有信息的传递,这对自恋者来说极度不安,因为所有的信息不再经过他们之手,这造成了无数冲突——自恋者与这位独立的共情者之间发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从未公开,当其中一些事情终于曝光时,自恋者又一次将责任推给共情者,因为他们从不会被指责,他们只看到共情者”对他们做了什么“,这些举动其实是共情者为了捍卫自己正当需求所做的回应,而自恋者则对他们自己不断的侮辱与不合理要求视而不见。
突然之间,所有来自社会的认可与金钱都停止流向自恋者,随着时间流逝,那位共情者持续靠自己的力量前进,凭借着实力与努力继续工作,共情者与自恋者之间的沟通就此中断,因为没有人能再承受那么多的负能量、无穷的要求,以及那些从未被公开的非理性争吵。
而这段沉默持续了数个月,直到某天,自恋者们对那位最后留下的共情者爆发出一场无法控制且非理性的愤怒攻击——因为对自恋者而言,世上最令他们恼火的事就是被”忽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争执,那位最后留下的共情者,只是在行使她身为一位独立个体的正当权利,因为与那些自恋者继续合作已经变得不可能。
然而,自恋者们突然捏造出一个故事,一个来自他们自身无根据的理论与混乱的想法编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毫无现实依据,态度极度不道德且极具倒退性。
他们并将一切错误都归咎于那位新来的共情者——因为对他们而言,是她破坏了他们的”事业“,而这本来就是一场生意,那些自恋者真心相信自己的理论,因为他们是自恋者,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缺陷与错误。
就如我先前所说的他们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唯一做的就是颠倒黑白、改编整个情况,好让所有事物符合他们那病态且不道德的叙事,他们只看得到共情者对他们说过的话,并指责对方对他们太”严厉“,却无法看见自己曾多么侮辱人与非理性。
他们的心思充满了过去那些共情者错误地给予的认可,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有权拥有所有的资讯—他们认为资讯都是他们的—也自认有权将他们的想法、错误结论与叙事强加于公众,并将公众当作武器来对付那位最后留下的共情者。
而许多大众也信了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所有厉害的自恋者一样善于说服,而大众信了,是因为根本不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了解我所说的一切,而我所说的,也只是整件事中的一小部分,因为绝大多数从未被公诸于世,全都被自恋者的滤镜过滤过了。
现在,大众开始要求那位最后留下的共情者出面说明,因为她正被大量扭曲误导的指控淹没,但事实上她无需解释任何事,因为她什么也没做错,她也不愿与任何人进入负面螺旋之中,那位最后的共情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从这种病态的自恋互动中解脱出来——而这就成了她的”罪“与”错“。
一次又一次,大众坚称那些自恋者的说法”很有道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些所谓”有道理“的说法,完全是建立在虚假与偏颇的叙事之上,而大众完全不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大众永远不该在只听到单方面故事的情况下就下结论。
也许这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指控那位最后的共情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为了牟利“——但那其实只是他们自身心态的映射。
因为当他们失去了”会下金蛋的母鸡“,也就是共情者,他们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利益。那位最后的共情者从未索要任何金钱,也永远不会索要,甚至连一台笔基本电脑也没要求过,她只是接受了来自大众自愿捐赠的资助,作为对她辛勤工作的感谢,而她也坦率地公开说明了她的用途,但这些用途后来又被扭曲,好让它们可以套入自恋者的叙事中,然而这些用途其实是在真诚无私地帮助他人,是符合伦理且正确的行为。
因此,自恋者想要阻止的这一切,最终会伤害整个人类。我必须重申一次:我从未向任何人索要金钱,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一种内在的需求,去写作与分享我的资讯,而且我们所有人只要还在地球表面上生活,或还与地球有所连结,就都需要金钱,至于有人建议”从小行星中提炼黄金“的方式,那是行不通的,因为你一旦拥有了黄金这种原料,仍需先将其出售才能兑换成金钱,而你若第二次再尝试出售,警察很快就会盯上你。
此外,还有那个叫做【首要指令】的规范存在,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浮现了:为什么需要金钱会被当成一种罪过?难道因为它不符合”精神层面“的要求了?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来自阴谋集团的把戏,目的是阻止那些正面的人在分享”非矩阵世界的事物、信息与艺术“的同时能够发展起来。
我依然需要吃饭,除此之外还要处理这一切,因为我收到的金钱其实并不多——这与那些自恋者的说法相反,即使金额不多,我也将它用于对人类真正有益的事情上。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有力论点“,因为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谎言与扭曲的事实之上,而且一如既往完全忽视共情者的视角,这一切只是每一段自恋关系在最终阶段的表现。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共情者的控制时,这种关系就会崩溃。
当他们无法再控制共情者、无法再剥削共情者时,他们就会诉诸毁灭的手段——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且残酷的思维模式,其逻辑是:”如果我不能拥有它,那么谁也别想拥有它“,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以自恋的方式试图摧毁这位共情者,但这位”最后留下的共情者“是所有人中最坚强的,她将会持续分享她的讯息。
无论发生什么事,那些自恋者会从那些盲从、不具思考能力的追随者那里得到他们所需的认可,但这只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那些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本质,或者厌倦了他们的负面言论、重复的资讯与一成不变的对共情者的旧有叙事。
他们现在攻击最后的共情者,声称”从一开始一切就是假的“,还说他们是所有共情者的受害者,但事实上,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掌控了整个叙事,也正是他们从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最终,这些自恋者将会孤身一人,除了自己那些不合逻辑的理论之外,什么也分享不了,只会在自己的怒气中溺毙。
我必须把这一切说出来,否则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版本。我们的这段故事——一段充满了自恋虐待、不合理的要求、威胁、持续的残忍与争吵的历史。
现在,我孤身一人,请谨慎选择你们想要站在哪一边,因为很遗憾,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双方对立的局面,与另一方不同,我从不向你们索求任何东西;你们所给予的一切都是出于自由意愿,而我非常感谢!
至于对方他们要求你们变得具攻击性,要你们仇恨、攻击、残忍——这一切全都建立在一些空洞的观念与理论之上,那些理论只存在于他们病态的头脑中,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之所以应该是真的,只因为是”由他们说出来的“。
请你们要有智慧!今天就说到这里,一如既往,谢谢你收看我的视频,如果你不喜欢,请取消订阅,也请不要转发,因为其他人也许会更有头脑。能看见这里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样做能让这个频道更加纯粹、得到更好的发展,我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们,献上我真挚的关爱与感谢,给我真正的挚友们。
玛丽女王
真实的、原初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2025年7月14日
本文连接:https://mariswa.net/empaths-and-narcissists-a-true-story-important-please-watch/
